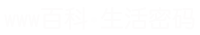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杨柳枯了 , 有再青的时候
|
|
|
杜宅原来的亭子栖身于楼宇间 |
|
|
|
杜宅现为东湖宾馆 |
|
|
|
杜宅原来的主楼 |
孙强南
杜月笙的豪宅
从行人如织的上海淮海中路弯进静谧的东湖路 , 走到尽头的70号 , 大门里就是位于东湖路和新乐路交汇口上有名的东湖宾馆 。 这里原是一处落成于1934年的私人花园豪宅 , 主人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杜月笙 。
当年杜宅的宅区呈锐角三角形 , 东边最宽 , 到西头两条马路的交汇处收缩成一个锐角 , 在角上有一座建在假山石上的中式亭子 , 据说这是杜宅镇风水用的 。 宅区北半部是三座坐北朝南连成一体的住宅楼 , 背面临街 , 楼高三层(现均已加到五层) 。 中间一座是最气派的主楼 , 东西各接着一座配楼 。 配楼高与主楼齐 , 但进深较小 , 南向的主立面装饰也要简单些 。 东配楼与主楼相连处开了个宽敞的门洞 , 过街楼下便是住宅的北门 。 在这一长排住宅楼的前方是一片约有一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大花园 。 当年这处豪宅在这一带法国租界幽静的住宅区里可谓是鹤立鸡群 , 气势不凡 。
据说 , 杜月笙曾计划安排他的四位太太分别住到主楼二、三层和两座配楼里 , 但豪宅建成后杜氏家事纷争不断 , 房子一直空关着 , 直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杜氏离开上海 , 杜家始终没有搬进去住过 。
1945年抗战胜利时 , 这里被国民党军统占用 。 归还杜月笙后 , 杜氏把它卖给美国人 。 在上海解放时 , 这里是美国领事馆 。 解放后 , 这里成为中共华东局招待所和上海市委招待所 , 改革开放后对外营业成为现在的东湖宾馆 。
这段杜宅的变迁历史 , 在附近住过的老上海们有人可能还记得 。 但是有一段历史知道的人大概不多 , 那就是: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到1945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 , 在杜月笙住宅里曾经办过一所中学——育群中学 。
我在1943年考入那所学校 , 在那里度过两年的学生生涯 , 经历了它从开张到停办的过程 。 我写这篇文字 , 是想对这段历史做一点拾遗补缺 。
豪宅里的学校
当年办学期间的杜宅和现在对外开放的东湖宾馆不同 , 沿东湖路高耸的围墙和紧贴在高墙后的松墙 , 以及长年严丝合缝地关闭着的大铁门 , 遮蔽着行人的视线 , 从马路上完全看不见宅内的景物 。 人车只能从新乐路的北门出入 。 人们走进北门 , 穿过门洞 , 进入花园 , 才能一览杜宅全貌 。 前几年我到上海 , 发现那个北门已经不见 。
育群中学的教学区 , 只占了主楼的一、二两层 。 主楼一层正中是个宽敞的大厅 , 厅内装修美观雅致 , 玻璃门扉晶莹透亮 , 花砖地面赏心悦目 。 这里是学校的礼堂 , 开学、结业等全校大会就在这里进行 , 我参加的入学考试也是在这里 。
大厅两侧有厢房 , 西厢房是校长办公室 , 东厢房则是我在初一时的教室 。 主楼二层面向花园的向阳面有三间正房和两间厢房 , 都用作教室 。 学校的办公室则安排在一、二层北面临街的众多房间里 。 东配楼里还有教员的单身宿舍 , 我在找老师时去过那里 , 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学生是不准擅自闯入的 。
那时宅区的花园里花木扶疏 , 绿草如茵 。 在东配楼前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 , 左右对称地掩映于楼前 , 四季常青 。 每逢春夏之交 , 满树花苞盛开 , 朵朵硕大洁白 , 熠熠满园生辉 。 广玉兰前有一方草坪 , 那是学校的主要运动场地 。 在上面布置了一个排球场 , 还放了一个篮球架供练习投篮用 。 我经常在早晨上课前 , 到那块草坪上和同学们踢皮球 。
在主楼的正前方有花坛等景点 , 学校在空隙处 , 挖了沙坑 , 安了单双杠 , 作为田赛和体操活动的场地 。 这些简陋的体育设施 , 对于当年上海市内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初级中学来说 , 还可算不错的 。
饱学的老师们
现在想来 , 学校在聘请授课老师和管理学生纪律方面还是下了功夫的 。
校长朱鹤翔先生 , 毕业于震旦大学 , 是比利时罗文大学博士 , 曾任职于北洋政府的外交部 , 并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法科当过教师 。
在学校聘请的教师中不乏饱学之士 , 当时的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先生也在教师之列 。 初一时我们班的英文老师是后来蜚声英语界的葛传槼先生 。 当年的他刚三十出头 , 清癯修长 , 长衫飘逸 , 讲课时发音清晰 。 他是我国研究英语惯用法的先驱 , 那时他已编写出版了《英语惯用法词典》 , 还是著名的《英汉四用词典》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 那本厚厚的四用词典我现在还在手头使用 。 葛先生后来又主编了久负盛名的《新英汉词典》 , 被誉为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三巨头”之一 。 最近我又从一位育群校友处得悉 , 他们班的英文老师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许国璋教授 , 也是重量级人物 。 由此可见当年育群中学教员阵容强大之一斑 。
令我难忘的是国文老师宋子敬先生 , 他循循善诱 , 对我鼓励有加 , 使我的语文水平有很大进步 。 我很喜欢听他满含激情的朗读和吟哦 , 我还能记得他在课桌间边走动边朗诵着朱自清作品《匆匆》的情景:“燕子去了 , 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 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 有再开的时候 。 但是 , 聪明的 , 你告诉我 ,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那情那景 , 我终生难忘 。 当年我涉世太浅 , 不能体味作品里包含的人生哲理 , 随着经历日增 , 才逐渐地有所体会 , 有时我甚至还会去想象当年宋先生朗诵这篇课文时 , 他可能怀有的沧桑情怀 。
学校里虽然没有实验室 , 但是我们的化学老师时常会端着一盘玻璃器具和试剂进课堂 , 为我们做化学试验的演示 , 使我对学习自然科学也倍感兴趣 。
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 , 我开始努力学习 , 成绩得到迅速提高 。 从小学时的中上水平上升到了班级的前列 。 在进育群中学后的第一个学年结束时 , 我就在学校礼堂里举行的全校大会上 , 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学行兼优的奖状 , 同时还得到一些奖品 , 其中有一本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线装拓本字帖 , 比较珍贵 。
热情的体育老师
学校对体育也比较重视 , 虽然全校只有一位体育老师张石芳先生 , 但是他却在狭小的场地上打造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局面 。
学校里组织了班际排球联赛 , 在布告栏里天天发布联赛战报 , 把学生们对排球的兴趣煽动得十分高涨 。 我们初一这个班居然能连胜高年级的对手 , 夺得亚军 。 我们班队的灵魂是我的小学同学王祖洪 。 我还记得在我们班队决赛失利后 , 布告栏的战报上用了“小霸王终遭滑铁卢”这样的标题来渲染和惋惜我们的失败 。
在育群中学里我的排球水平有了提高 , 在班队里算是个骨干 , 不过我从小学开始 , 始终只能当个班代表队的队员 。 而王祖洪则在八年后的1951年就入选国家排球队 , 成为国家队的队员 。 在1956年国家体委把国家男排划归北京市的时候 , 他又被委以北京男排第一任主教练的重任 , 成为享誉我国排球界的一代耆宿 。
记得我们的张老师还有一项专长是撑杆跳 。 他在小小的沙坑前培养出了几个身轻飞燕的撑杆跳好手 , 这在当时是比较稀罕的 。
诡异的日本老师
学校成立之初还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语 。 那个日本人就住在学校里 , 平日里讲着中国话 , 常和大家一起玩单杠、练体操 , 尽力博取学生们的好感 。 有一次我还见到他拿出日本人练劈杀的头盔、手套、衣服和竹竿 , 给学生们演示劈杀动作 , 有个胆子大的学生还跟他学了几招 。 然而大家对于上日语课始终是很反感的 。
一天 , 学校突然召开全校大会 , 原来是这位日本老师要上前线了 。 在校长的开场白之后 , 只见那个被校长称为绪方大佐的日文教员 , 身穿军装 , 足蹬长靴 , 腰佩军刀 , 咯噔咯噔地走上台去 , 哇哩哇啦地讲了一通日本话 , 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面目 。 没过多久 , 听到了一个传闻:他们的运兵船在太平洋里被击沉了 。
纪念册里的关爱
在我读初中的那个年代里 , 学生们喜欢拿着一本精致的小纪念册子请校领导和老师们题字 , 而师长们也总是有求必应 。 那时的老师们大多熟读古文 , 工于书法 , 他们都会很认真地用毛笔字为学生题写 , 内容都是一些鼓励学生努力向上的警句格言 。 在他们工工整整的题字里 , 透现着他们的学识卓见和对学生的关爱期待 。 有的老师还会巧妙地把学生的名字嵌在意义深刻的题词中 。 记得国文老师宋先生给我的题词是:“舒缓其德 , 南方之强” , 寓意于《中庸》的“南方之强” , 含义深长 。 (原文是:“宽柔以教 , 不报无道 , 南方之强也 , 君子居之” 。 )
还有一位历史老师高先生给我的题词是一双工整的对句:“强项立节重 , 南面拥书多” 。 上联来自《后汉书·酷吏传》中所记东汉光武帝时不畏权势、敢于执法的洛阳令董宣的强项令故事;下联则出自《魏书·逸士传·李谧》中饱学多才、博览群书的北魏逸士李谧的“丈夫拥书万卷 , 何假南面百城”的名言 。 这个期望真是太高了 。 记得有位名字叫亦方的同学 , 老师给他的题词也是一双对句 , 下联是“君子亦方亦圆” , 也有着很深的哲理 。
非常可惜的是 , 我的那本满载着初中时代美好记忆的珍贵纪念物——上面题满了初中时代校长和老师们赠言的纪念册 , 因为上面有学校领导胡文耀、朱鹤翔以及不知底细的老先生们的题词 , 被我在“文革”初销毁了 。 但是 , 那段深藏在我心间的峥嵘岁月的记忆却是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驰而逐渐淡漠的 。
瞬间劳燕分飞
在1945年暑假里的一天 , 当我走进弄堂准备回家时 , 忽然听到邻家收音机里传出了声震屋外的广播声 , 有个日本人在讲话 , 原来是日本投降了 , 这使我兴奋不已 。 但过了不久却传来了育群中学要停办的消息 , 我赶紧到学校去探听究竟 。 只见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学生 , 大家都被腰别手枪的便衣挡在门外 , 不准进学校一步 。 最近看资料才知道 , 那时的杜宅已为国民党军统所占用了 。 就这样 , 在一个班里相聚两年亲密无间的同窗好友们 , 就像一颗突然爆炸的炸弹的碎片 , 在一瞬间就无序地散向了四方 。 大家既没有向老师告别 , 也没有互道珍重 , 就劳燕分飞 , 各奔前程了 。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育群中学的少年好友们 。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找到了打排球的王祖洪 , 他正担任着北京女排的总教练 。 当年我们女排的训练条件远不如现在 , 只见他正站在露天的排球场边 , 关注着几个年轻教练带着一群滚得满身是土的女孩子练球 。 那时我们都已年过五十 , 谈话间对流逝的岁月都感叹不已 。
世事纷纭 , 韶华不再 。 懵懵懂懂的少年岁月虽已如烟飘散 , 但是 , 隐隐约约的陈旧记忆仍会随时涌现 。 在不知不觉间我已进入耄耋之年 , 忽然想起来要写点儿东西 。 我试着到网上去检索那些熟悉的名字 , 找着找着 , 果然捡到了几个飞向四方的碎片 。 那位被老师要求“亦方亦圆”的同学 , 大学毕业后当了鞍山市化工二厂的厂长 , 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模范共产党员 。 一位一起踢皮球的同学 , 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 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主席 。 啊 , 原来那些四散的碎片都藏在各处散发着各自的光芒呢!
还有很多同学 , 他们又在哪里呢?记得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王丹凤的弟弟 , 我从他那里要到了一张他姐姐手推自行车的签名艺术照片 , 照片相当大 , 够交情吧!那位同学还在上海吗?
办学意图何在
作为学生 , 我对育群中学的办学背景一无所知 。 如果从它存在的时间段来猜测 , 应该有一定的办学意图吧 。 那所育群中学成立于日本人1943年1月进入租界之后 , 停办于日本投降之际 。 那么 , 为什么要在乱世纷纷的年代里来办这么一所只能存在短短两年的学校呢?是谁愿意在这个时候拿出大钱来置教具聘教师创办这一所学校呢?住宅的主人为什么舍得让众多淘气的孩子涌入崭新的厅堂居室里和花圃草坪间去肆意嬉戏践踏呢?我猜测不了 。
这些问题也许只能请研究上海历史的专家学者们来解答了 。
供图/孙强南
推荐阅读
- 凿壁偷光的匡衡,后来怎样了?成了贪官为害一方
- 古人VS地震,整个人都不好了
- 你不知道的李清照:除了写诗,还是赌神和酒神
- 在黄埔军校默默无闻,抗战时快速晋升,三大战役他参加了两场
- 法正:蜀汉立国第一人,贡献了蜀汉疆土的90%
- 趣读丨微信新增表情火了,如果翻译成古诗词,你猜是哪句?
- 楚霸王项羽26岁前干了哪些事儿?
- 古人VS地震,整个人都不好了,康熙带头,纷纷写下忏悔书
- 考古现实版的九层妖塔,为何盗墓贼挖到第二层,就挖不动了?
- 张衡的地动仪,真能预测地震吗?它为何被移出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