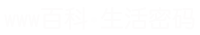被遗忘的民国才女遗书:《我是幸福的》
编者按:人们谈起民国才女总是津津乐道 , 无论是惊世的才情 , 还是秀丽的容貌 , 都让民国才女在中国文学界大放异彩 。 然而在沦陷区这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领域里 , 相对于张爱玲、苏青等人还有一位较为陌生的女作家——雷妍 。
雷妍(1910-1952) , 本名刘植莲 , 笔名刘咏莲、刘植兰、芳田、端木直、田田、田虹等 。 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 , 1937年从湖南回北平娘家生孩子时 , 适逢“七七事变”而不能南返 。 生活的重压反而促使她拿起笔在虚构的世界中释放着她的才华 。 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使她迅速蹿红 , 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作家 。 新中国成立初期 , 正是文坛重新绽放的时刻 , 她却不幸陨落 , 以致后世对她知之甚少 。
|
被遗忘的民国才女遗书:《我是幸福的》// // |
雷妍所处的时代本不是“罗曼蒂克”的时代 , 当时的人们认为把握住生活的情绪是最现实的 , 也是最不易幻灭的 , 他们重视生活劳作 , 却不在意情感宣发 。 所以 , 女性作家大多希望“从柴米油盐 。 肥皂 , 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 雷妍却是特立独行的存在 , 即使身处逆境 , 她关注的并不只是身边的柴米油盐等琐碎而世俗的细枝末节 , 她把所有的柔情与辛苦劳作相结合 , 将笔墨更多的聚焦在人性的纯良上 , 写得浪漫缱绻 , 下笔即成桃源 。
如果说 , 以张爱玲等人为代表的作品是一根刺 , 针针见血 , 那么 , 雷妍的作品则是在治疗疼痛的麻醉剂 。 起码 , 在一个硝烟弥漫的相对封闭的沦陷区中 , 她以手中的笔不卑不亢地为世人构造起一个充满希望的、乐观向上的世界 , 在高压的文化政策中以构造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间带给世人对于家乡、对于国土的深深眷恋 。 而这一切正是她以悲悯的宗教情怀看待人性的丑恶和山河破碎的喧嚣世间 。
雷妍在去世前的那年春天 , 以已经参军到抗美援朝前线的大女儿刘琤的口吻 , 用笔名“田虹”写出副标题为《一个中学生的笔记》的自传体小说《我是幸福的》 , 追述了自己多年苦难的生活经历 , 表达了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 。 在小说结尾处 , 她满怀激情地自语:“最敬爱的毛主席 , 我是幸福的!!!我一定在您的旗帜下 , 为更多人的幸福而奋斗!!!”这当是“走得太仓促”的雷妍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心音 。
(遗作《我是幸福的——一个中学生的笔记》节选)
我叫徐敏 , 十八岁了——是中国的习惯算法 , 那就是还不足十七周岁 。 在我填入学证、保证书的时候总是写:“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生于北京 。 ”可是母亲在旁边总要给我补充一句:“那年七月一日是阴历的五月二十日 , 石榴花都开啦 , 天气闷热闷热的……”我每次听她这么说 , 心里就想:“妈妈记得真清楚 , 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有的时候她也会沉痛地说:“那正是"九一八"后的第三年 。 北京街上有许多东北难民 , 我正在大学读书 , 因为要生你就休学了 。 可是我总和同学们在一起做募捐工作 , 然后送给在街头流浪的东北同胞 。 有一次在吉林会馆慰问受难同胞 , 两大群警察把我们包围了 , 把一个姓钟的同学逮走 , 我被人挤倒在台阶上 , 当天晚上你就出世了 。 可是姓钟的同学一直没回来 。 听说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 反对"不抵抗主义" , 她是被他们——蒋介石的特务给害死了……”我一听这个话就难过 , 妈妈的脸也特别阴沉苍白 。
真的 , 那时候的年轻人多么不幸啊!我的父亲就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叫自来水笼头浇了一身水 , 在小胡同里困了半宿 , 已经冻成冰人啦 , 又在警察局拘留了五天 , 回家以后 , 就得了严重的肺炎 , 一直躺着不能起床 。 一九三六年年底他已经有些起色了 , 又因为夜里查户口和一个警察争辩了一次 , 当时他就又吐起血来 。 一九三七年初春的一个晚上 , 他就死去了 。 从此 , 我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 。
父亲死后两个月 , 妹妹就出世了 。 那正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十六日 。 又过了三个月就是“七七事变” , 日本鬼子侵入了北京城 。
我们母女三人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 , 外祖父母都是最慈祥和善的 。 还有一个白头发的太姥姥——曾外祖母、一个舅舅、两个姨 。 在我乍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七七事变” , 外祖父、舅舅和两个姨就都走了 , 离开北京 。 妈妈说他们不走不行!家里只剩下老的老、小的小 , 生活可成了问题 。 本来外祖父是个文教工作者 , 从来没有积蓄 , 舅舅和姨们走的时候还都是中学生 。 生活的担子就紧紧地压在母亲肩上 。
一个冬天的晚上 , 大门叫人砸开 , 进来许多人:有鬼子 , 也有地痞流氓 。 有的喊着“查户口” , 有的喊着找“不良分子” , 可是把屋里生活用的东西都抢走了:衣服、被褥、书籍、水壶、锅、碗……全没有了!眼看天气一天冷似一天 , 就要挨冻啦!可是妈妈总是劝外祖母说:“怕什么?等打走了鬼子 , 咱家人都回到北京以后 , 要什么没有呢?”妈妈在姥姥面前总是乐观的 。 可是她把夏天的衣服包起来跑到当铺里去当 , 拿很少的钱回来日用 , 有时候当不了什么钱她就不当 , 空手回来找点东西卖给打小鼓的 , 我看她的脸色就没有劝姥姥的时候那么高兴 , 甚至特别苍白叫我害怕 。
冬天勉强过去了 , 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屋里睡 , 天还没黑就把大门锁上 , 自从家里的小狗小黄叫日本鬼子打死以后 , 院里更空落落得可怕 。 大约是旧历的正月 , 天仍然很冷 , 不到六点天就黑了 , 我们在床上玩手影 , 妈妈在刷碗的时候 , 忽然大门被擂得山响 。 我们互相望着像大祸临头一样 , 我和小妹妹都哭了 , 两人一起往外祖母怀里钻 。 曾外祖母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 , 耳朵虽然聋看我们这样子也急得不行 。 妈妈一边安慰我们说:“别怕!”一边强自镇静地擦着手 , 颤声说:“谁呀?”外边是浑浊的鬼子的声音:“开门!大大的 , 要紧的……”妈又问:“你找谁?”外边不回答 , 使劲擂大门 , 电表的保险丝震坏了 , 屋里一片黑暗 。 我在外祖母怀里感到外祖母也在发抖 。 妈妈忽然大声说:“不说找谁 , 不给开门!”曾外祖母小声叫着妈妈的小名说:“青儿!你别出声了 , 叫人听出咱们家连一个男人都没有……”叫不开门 , 外面的人走了 。 第二天街坊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是鬼子卖仁丹、臭虫药 , 捎带着调查……不开门他们还会来的 。 ”我们的门户更紧了 。 但是曾外祖母吓得病了一场 , 一个月才好 。
为生活所迫 , 妈妈用自己早年存的花布做小孩衣服 , 到中原公司和百货公司去寄卖 。 但是人家不要 , 人家要日本货 。 妈妈又到国货售品所去 , 过去外祖母家买什么都是去王府井国货售品所 , 所以有熟人 。 他们答应给寄卖 。 但是东西放了半个多月才卖出五件 。 妈妈本来答应卖了东西给我买糖 , 现在只好用这点钱买杂和面 , 我看见妈妈背着灯掉眼泪 , 我也在被窝里哭了 。 之后国货售品所被日本鬼子硬逼着改成“百货售品所” , 熟人也换掉了 , 妈妈做的东西更卖不掉了 。
春天来了 , 东西更贵了!妈妈上当铺去得更多了 。 一次妈妈带我去当外祖父的皮袍子 , 妈妈叫他们写五十块钱 , 他们只写了八块 。 高高的柜台看不见人 , 只听见一个难听的声音说:“就八块 , 多一个子儿也不要!”妈妈低声和气地说:“这么好的皮袍子 , 您多写两块吧 , 十块 , 行不?”里面的声音说:“甭想!八块 , 你当不当?”妈妈叹口气说:“八块就八块吧 , 我当了!”那声音又说:“二分五的利息 , 三个月死当!”妈妈大为吃惊地说:“仨月?不是一年半吗?”那声音说:“东洋规矩!”妈妈说:“什么时候改的东洋规矩?”“什么时候?你当不当吧?”妈妈的声音像是要哭:“当啊!”一阵算盘声 , 从柜台里伸出一只手来 , 递给妈妈一张画着字的纸和几张破票子 , 就把外祖父一件好看的蓝绸子面、花毛毛的灰鼠皮袍子抓走了 。 我抬头一看妈妈的脸像纸一样白 , 用她冰凉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 走回家去 。
家里再没有东西可以当了 , 已经当了的东西根本赎不起 。 妈妈再三托人 , 总算得知胡同里的一家人要一个家馆先生 , 妈妈去了 。 但这家人孩子非常多 , 什么程度的都有 , 国文、数学、英文 , 都要教 , 外带给他们家记账、写信、给少奶奶织毛衣、陪老太太聊天……不到两个月 , 妈妈病倒了 。
在妈妈生病的一个五月的晚上 , 又有人叫门 , 外祖母问:“是谁?”“查户口!”不一会儿 , 进来一大屋子人 , 有鬼子、有便衣——后来我知道那是特务和伪警察 。 他们一边看户口单子一边问:“户主上哪儿去了?”妈妈说:“回原籍了 。 ”“户主的儿子呢?”“也回原籍了 。 ”“你是什么人?”“我是户主的长女!”“徐青?出阁的人啦 。 你的男人呢?”“死了 。 ”他们停了一会儿没言语 。 我当时心里真难过 , 要是父亲不死 , 也许日子好过些 。 这时一个便衣又问:“男人都回原籍啦?哦?女的可留在北京 , 真邪门儿!”妈妈镇静地说:“男人都有病 , 在外头没法子过 。 ”“女的倒有法子过?你们指着什么过日子?有钱 , 对不对?”妈妈看了他一眼说:“哪里有钱?教家馆!”便衣把脸一拉说:“问你话是客气 。 不实说 , 可有地方叫你说 。 ”“确实没钱 。 ”便衣把眼睛四下一扫说:“没钱还住独门独院?”“我们是给一个同乡看房子 。 ”“同乡也走了?又回原籍了对不对?甭理她 , 给我搜!”日本鬼子跟这个特务叽里呱啦说一阵子 , 就搜起来 。 一个熟识的老警察走过来 , 悄悄对妈妈说:“一样话十样说 , 你可不能动气呀!”
他们把衣柜打开 , 里面什么也没有 , 又打开箱子、抽屉 , 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 倒是在相片本里发现一张舅舅穿着学生制服的四寸半身像 。 鬼子对特务说:“八路的……”特务恶狠狠地对妈妈说:“这是谁?”“我弟弟 。 ”“不像有病的!他回原籍了?还是去什么地方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 ”那个老警察说:“我想她也不敢撒谎 。 咱们今儿个可还要查好几家哪!要没搜着什么可该走啦 , 别把别处耽误了!”特务瞪了老警察一眼说:“你忙什么?”老警察连忙笑着说:“我哪儿敢忙啊?我是户籍警 , 只是各尽各心 。 您要准说不忙 , 咱就在这儿泡!”特务哼了一声跟另一个便衣又搜了半天 , 才说:“这房子够好 , 算你们二等户!二等户要给皇军献七十斤铜!明天送到保长家!”妈妈说:“七十斤?连七两铜也没有啊……”但是他们都已经走到门外去了 。 特务又回头大声说:“没有?!到宪兵队去说!”妈妈关上门回来望着屋子被搜得七零八落的样子 , 呆呆地站了好半天才抱起我来说:“孩子 , 不用怕!国家被人家占了就是这个样!以后这种事少不了!要学得勇敢起来!”外祖母紧张地说:“七十斤铜可上哪儿弄去呀?”妈妈像是横了心似的说:“上哪儿弄?就是没有!到时候再说吧!我头都疼了 , 咱们快睡吧 , 都十二点了!”第二天是个好天气 , 院里的江西腊梅开得美极了 。 妈妈正预备给家馆去上课 , 保长来了 , 问要献的铜准备好了没有?妈妈说:“没有!”保长是个老滑头 , 见妈妈态度很强硬倒和气起来说:“咱们街里街坊的 , 瞒上不瞒下 , 谁也不是他妈日本人的亲爸爸 , 左不过是没办法的事儿 。 您先紧着家里的铜器拿出点来送去 , 也省得找麻烦!好鞋还不踩臭狗屎呢!”妈妈想了一下说:“折现钱行不行?”保长装模作样地摇着他的胖脑袋说:“哟!那得合多少钱呢?”妈说:“多了也没有!我昨天领了薪水一共十八块钱 , 给我们留点过日子 , 您看着拿吧 。 ”保长不痛快地说:“这么点钱!您自己到段上去说吧!”妈妈生气地说:“行!我自己去!”保长一看有点后悔自己刚才把话说绝了 , 又往回找补着说:“瞧您!还是先到我那儿办个手续吧!”妈妈只好跟他走了 。 外祖母不放心地追出来说:“青儿!办完手续先回趟家 , 再去上课!”
但是都到下午了 , 妈妈还没回来 。 家馆那边还打发听差来找妈妈 。 外祖母急坏了 , 把我和小妹妹交给曾外祖母 , 准备出去找妈妈 。 偏巧妈妈这时满身是土 , 疲劳不堪地回来了 。 原来保长带她去办手续、交钱 , 又去献铜处办手续、交钱 。 每一处都等好长时间 。 好多人因为没有铜可“献” , 都被带到宪兵队去 , 有的当场就被鬼子打了 。
当时许多人家都不肯送子女上日本人管理的学校 , 有点条件的请家庭教师的风气很盛 。 妈妈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了两个家馆的工作 , 她更忙了 。 往往天都黑了 , 西北风吹得电线发出野兽般的吼声时 , 妈妈还不回家 , 家里冷清得怕人 。 白面已经没有卖的了 。 买小米面、棒子面 , 买盐、买煤 , 甚至于买杂和面都要排队 。 杂和面里掺很多沙子 , 做窝头时先要把沙子用水沙出去 。 到年根底下连杂和面都没有了 , 配给各户一种混合面 , 是由花生皮、豆渣、荞麦皮、糠、谷皮等碾碎混合而成 , 自然沙子更多 。 曾外祖母是八十多岁的人 , 就这样把肠胃吃坏了 , 泻肚二十八天去世了 。 临死她用手比成一个圆圈 , 费力地说:“……团圆……”妈妈哭着说:“弟弟、妹妹就是为了将来大家团圆才走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曾外祖母去世后 , 妈妈向两个家馆预支了钱买的棺木 。 入殓的时候 , 妈妈用手顶着棺材盖板 , 不断地向曾外祖母说:“姥姥 , 他们就会回来!”虽然入殓了 , 却不能下葬 。 原来妈妈忘记给段上那些头头脑脑“车马钱” 。 妈妈在段上蹲了大半宿把买棺材剩下的钱给段上的人交上 , 才领下来“抬埋证” 。
曾外祖母去世后 , 外祖母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掉眼泪 , 看她那么伤心 , 我就领着小妹妹躲到石榴树下一起哭 。 我问妹妹:“你知道谁叫咱们家一家人不在一块的?”妹妹仰着挂满泪水的小脸说:“日本鬼子!”“对!你长大干什么?”“打日本!”我就抱住她 , 给她擦眼泪 。
一九四三年 , 我插班上了小学三年级 。 有一次 , 妈妈送我上学 , 路边上躺着两个饿倒的人 。 妈说:“你看 , 有一个还在动哪!”她拉我赶快跑过去 。 一看 , 是一个才三十多的年轻人 , 瘦得皮包骨 , 我把手里的窝头递给她 , 他看了看 , 没有动 。 妈问他:“你是渴吧?”他用力地闭了闭眼睛 。 可是我们并没有带水呀!妈妈用身上仅有的几百元破票子(这时已经改用“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了) , 跟旁边一个卖酸枣汤的好说歹说地买了一碗酸枣汤 , 又要了几块冰 , 给这个“路倒”送去 。 但是妈妈叫他喝水他不动 。 妈妈把冰放在他手里 , 他睁开通红的眼睛 , 把冰块往嘴里塞 。 他是在发高烧!妈妈赶紧又喂了他酸枣汤 , 他喝了以后好像松了口气 , 用眼睛看看我们 , 像在表示感谢 。 但等我放学回来时 , 这个人往前爬了几个大门 , 却直挺挺躺在那儿 , 死了 。
小学校里有很多小朋友 , 老师也和蔼 , 我真喜欢上学;但是有一个日本教官非常厉害 , 每天早上他都要对我们“训话” 。 他那凶恶的态度 , 吓得每个小朋友都把脸绷得紧紧的 , 老师的脸更难看 。 不久日本统治下的伪政府搞什么“强化治安运动” , 并强迫我们背“强化治安条例” 。 那么长的“强化治安条例”我们都背不下来 。 一次 , 日本教官来我们班检查背“条例”的情况 , 见我们都背得不好 , 当场就把老师带走了 。 之后老师一直没回来 , 听同学们偷偷地说:老师是被带到宪兵队去了 。 我们想老师 , 她对我们那么好!但是她却不知下落了 。 我难过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 妈妈下决心不叫我上学了 。 她自己下了家馆课再教我和妹妹读书 。
可怜的妈妈 , 她太累了!白天她教家馆 , 回来还要洗我们的脏衣服、打扫房间、帮外祖母买菜、做杂务 , 所以我从七八岁开始就帮妈妈做家务 。 而妈妈呢 , 从不叫苦!晚上做完这些杂事她就在菜油灯下给我们读《爱的教育》《稻草人》……有时外祖母也来听 。 但是 , 我和妹妹一睡下 , 妈妈和外祖母就说另外的话了:“日本打得可不好!快完蛋了!”“日本最近在战场上死的人可多了!”“日本女人为了不让她们的男人去打仗 , 有的开始卧轨啦!”“弟弟妹妹们不久就快回来啦!”妈妈担心我们会到外面说 , 从来都是背着我们和外祖母说 , 她不知道我其实也恨日本侵略者!我也不会跟什么人都瞎说的 。 看看!日本鬼子的日子果然越来越不好过了 。 现在 , 地面上说怕美国飞机来炸 , 叫家家挂黑窗帘 。 我们因为没有钱 , 买不起窗帘 , 就用报纸刷上锅烟子挡在窗户上 , 结果保长说我们违抗命令 , 怎么辩也不行 , 还是罚了十块钱 。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 外祖父、舅舅、两个姨也都没有消息 。 一九四四年的端午节 , 外祖母突然病了 , 发高烧、说胡话 , 不断地叫着舅舅和两个姨的名字 。 妈妈急坏了 , 第二天早上神秘地把一封信交给我 , 说:“敏儿!你到大门外去 , 然后拿着这封信往院里跑 , 你要边跑边说:"妈妈!给您一封信!"这是给姥姥治病的药!懂吗?你姥姥的病完全是因为想舅舅他们想的 。 ”我使劲地点点头 , 想让妈妈知道 , 我是大孩子了 , 懂妈妈的心 。 外祖母是不识字的 , 这样做也许她的病会好呢!我按妈妈教的从院门往里跑 , 一边大声喊着:“妈妈!您的信!”妈妈说:“拿进来吧!”外祖母从床上抬起头来说:“谁来的?”妈妈假装高兴的样子 , 笑着大声说:“弟弟来的!小敏给姥姥念念!”我看了妈妈一下 , 大声念道:
“母亲老大人:我及两个妹妹在外都好 , 我们的买卖也很顺利 , 和父亲大人也有书信来往 , 请大人勿念……”
我念完以后 , 外祖母对妈妈说:“呃!他们好像知道你姥姥死了似的 , 怎么一个字也没提哪?”妈妈的眼睛里满是眼泪 , 可是她却笑着说:“您可真不知足 , 好容易来一封信 , 哪能问得那么全呢?他这封信不定走得多么慢呢!”外祖母问:“这信走了多少日子?”妈妈想了一下说:“也许日子不太多吧 。 ”外祖母说:“可不是吗!信皮还那么新哪!”说也奇怪 , 外祖母的病第二天就好了 。 善良的外祖母啊 , 她不知道那是一封假信啊!
外面很乱 , 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就很少出门了 , 待在家很寂寞 , 但也没有法子 。 以前妈妈带我们去北海公园时 , 见到日本浪人在那里喝酒、乱唱 , 军官则带着女人在那里吃、闹 , 做着让人看不下去的动作 , 妈妈总是带我们绕开 。 现在 , 就不只如此了 , 出门连安全都没有保障 , 我和妹妹索性不出去了 , 一切都等着打走鬼子再说、再玩、再欣赏 。 我们一定在家好好学习 , 等着外祖父和舅舅回来 , 用我们的学习成绩叫他们高兴!虽然我不出去 , 但以前的同学有时还来看我 , 听他们说 ,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真叫鬼子给害死了 , 有人在东城一个宪兵队的后墙外面 , 发现了老师的尸首全身肿烂 , 已经不成人形了 。 老师的妈妈天天去那儿哭 , 后来家里的人怕鬼子把她打死 , 只好把她关在家里 。 我们的好老师!我总忘不掉她教我们写字的样子:穿着短袖的麻布大褂 , 抬着手指着黑板上大个儿的“马”字 , 有腔有调地说:“一横、一横又一横 , 一竖再一竖 , 一个大拐弯 , 一点、一点、一点 , 又一点 。 ”然后用她那红苹果一般滋润的脸笑着看我们 , 风吹着她的短发 , 她笑眯眯地问:“会了吗?再说一遍:一横、一横又一横……”有一次 , 我在操场上摔倒了 , 她连忙把我抱起来说:“不怕 , 老师帮你掸掸身上的土 。 ”她看我要哭就又说 , “好孩子咱们都大了 , 摔一下不要紧 。 ”老师这样安慰我 , 我也就不哭了 , 反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 从她身上跳下来 , 赶紧就跑 。 老师把我叫住 , 和气地说:“徐敏 , 老师刚才扶你 , 是帮助你 , 你应当谢谢老师 。 ”我赶紧给她鞠了一个躬 , 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 她在后面紧着说:“你刚才摔了跤 , 不要再跑啦!”这么好的老师 , 今后再也看不见了 , 让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给杀死了!!
这时候的北京人 , 都饿得皮包骨了 , 每天妈妈下班回来 , 老远就能看见她那深陷的眼眶子和消瘦的脸颊 , 她那曾像黑缎子一般的乌黑头发 , 现在像一蓬乱草顶在头顶上 。 中国自己的军队快回来吧!
本文节选自《白马的骑者》 , 磨铁图书出品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