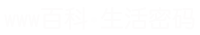古代女性过节的“穿戴之美”
李汇群
时值阳春三月 , 大地春回 , 大街小巷行人如织 , 而女性服饰更是呈现出一派五彩缤纷的春和景象 。 明天 , 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 。 与古代女性相比 , 现代女性的境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 在时尚领域也有了更多选择与表达的自由 。
在妇女节来临之际 , 梳理古代女性过节的“穿戴之美” , 回顾她们所经历的“时尚史” , 既是为了真正认识传统文化 , 撷取并传承其精华 , 也是为了思考服饰所折射出的社会观念变革 , 寄望于女性群体更加独立且美丽、奋进而优雅的未来 。
顺应天时:簪四时花 , 着四时衣
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 , 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 , 农业一直是中国的国之根本 。 春种秋收 , 顺应天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核心 , 在古人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 都印上了深刻的时间烙印 。
以服饰而言 , 古人爱簪花 , 花以时令鲜花为尚 。 春天以桃花、杏花等为多 , 唐代刘禹锡写桃花“山桃红花满上头 , 蜀江春水拍山流”(《竹枝词》) , 宋代陆游写春天里小贩叫卖杏花“小楼一夜听春雨 , 明朝深巷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 。 夏天则以莲花、茉莉等为盛 , 宋代洪咨夔写词云“正好簪荷入侍 , 帕柑传宴”(《天香》) , 苏轼写海南风光 , 有“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题姜秀郎几间》)佳句 。 秋天最受喜爱的花 , 当推菊花 , 所以唐代杜牧形容重阳节的景象是“尘世难逢开口笑 , 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 。 待到冬天 , 梅花绽放 , 暗香浮动 , “袖笼玉梅三百朵 , 为卿低插鬓云傍”(清代孙原湘《簪梅》) , 玉梅低插 , 为鬓云增色 , 也是一份难得的冬日雅致 。
除头上插戴之外 , 古人穿衣也往往依照时令季节而调整 , 对时季的强调 , 发展到明代 , 遂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穿衣制度 。 晚明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详细记载了明代宫廷的穿衣细节:腊月廿四日祭灶到正月初一 , 宫眷内臣穿葫芦景补子和蟒衣;正月十五元宵节 , 穿灯景补子和蟒衣;三月初四 , 换穿罗衣;清明节 , 也称“秋千节” , 插杨柳枝于鬓发上;四月初四 , 换穿纱衣;五月初一至十三 , 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 , 初五端午节赏石榴花 , 佩艾叶;七月初七七夕节 , 穿鹊桥补子;八月 , 赏秋海棠、玉簪花;九月初四后 , 换穿罗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 , 并抖晒皮衣 , 制衣御寒;十月初四日 , 换穿纻丝;十一月 , 百官传带暖耳 , 冬至穿阳生补子蟒衣 。
补子 , 是明清官员在常服的前胸后背上缝制的方形或圆形图案 , 原用以区别官位等级 。 从《酌中志》的记录来看 , 明朝宫廷女眷也可以穿补子蟒衣 , 而补子图纹则根据节令的变化不断调整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代应景纹文化 。
诸色纷呈:五时衣 , 色相宜
明代应景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频繁出现 , 说明当时人对四时变迁、春去秋来的自然变化极为敏感 , 这是中国传统天人感应思维的某种表征 , 而这种敏感不仅表现在以图纹迎合天象 , 还反映在色彩和时令的对应中 。
早在西汉 , 皇帝的着装色彩已经根据季节规律变化 , 天子服制“大抵以四时节气而为服饰之别 , 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 到东汉 , 四时衣变成了五时衣 ,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就提到阴太后的遗物中有五时衣 。 “上有所好 , 下必甚焉” , 传统社会是尊卑有别的等级社会 , 服饰传播大抵也遵循从上至下的传播路径 , 宫廷喜好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并左右了民间习俗 。 所以 , 到南北朝时期 , 江南一带“嫁娶新妇 , 必有五时衣……五时者 , 谓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也”(参见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笔》) 。
除了大致的季节色彩之外 , 在某些特殊的节日 , 为营造独特美感 , 女性会偏好某种服装色彩 。 比如元宵节和中秋节 , 都是时逢十五 , 明月当空 , 女性偏好穿白色衣裳以衬托夜色 。 元宵节穿白的习俗可能始于宋代 , 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述 , “元夕节物 , 妇人……衣多尚白 , 盖月下所宜也” , 相沿成习 , 明代女性元宵节爱穿白衣 , 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习俗的小说中也多有记述 。 如《金瓶梅》假托宋朝背景写明朝故事 , 书中对女性元宵节穿衣有生动的细节写照:第十五回 , 西门庆的妻妾元宵节登楼看灯 ,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 , 娇绿段裙 , 貂鼠皮袄 。 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 , 蓝段裙”;第二十四回 , 正月十六晚上 , 西门家的女眷出门走百病 , “月色之下 , 恍若仙娥 , 都是白绫袄儿 , 遍地金比甲” 。 孙殿起编辑的《北京风俗杂咏》中解释走百病 , “正月十六夜 , 京师妇女行游街市 , 名曰走桥 , 消百病也 。 多着葱白色绫衫 , 为夜光衣” 。 可见 , 正月十六女性出门走百病 , 是明代以来的北京习俗 。 《金瓶梅》的故事背景依托为山东省 , 但距离京城不远 , 加上商贸流通频繁 , 因此习俗与京城相同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红色 , 也是女性过节所喜爱的颜色 。 红色在中国传统色彩中属于正色 , 代表着典雅、端庄 , 古典诗文中关于“红裙”、“茜裙”、“石榴裙”的记录不胜枚举 , 可见红色之受欢迎 。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 , 宫女多穿红袄 , 搭配青色下裙 , 也就是“红配绿” , 形成强烈的撞色冲击效果 , 尽显热闹氛围 , 而后方背景更是大片渲染红色 , 足见红色在传统色彩体系中的重要性 。 从图中能看到 , 除了红配绿宫女服装也常以绿色配蓝色——绿色代表草木色 , 意味着生命勃发 , 蓝色意味着洁净祥和 。 这几种颜色 , 差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偏好的节日服饰颜色 。
各归其位:定尊卑 , 别上下
红色 , 在传统服饰体系中还有另外的含义 。 如上文所述 , 《金瓶梅》中的女性大都喜欢穿白绫袄儿 , 但西门庆的正室夫人吴月娘 , 在妻妾同堂的场合 , 却往往是一袭红衣加身 。 相比较而言 , 红色稳重 , 白色飘逸 , 青春貌美的女性 , 通常会更偏好白色 , 以彰显活泼灵动的气质 。 吴月娘正值妙龄 , 本应如同其他人一样喜欢白色 , 但为了凸显自身的正室地位 , 她不得不压抑自我内心对情感、美丽的自然需求 , 而代之以礼教的面具 。 可以说 , 红色和白色的对峙 , 折射了妻妾之分、嫡庶之别 , 而这正是传统服饰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中 , 服饰是区别身份的重要标志 。 比如同样是贵族女性戴的凤冠 , 却因为身份的不同 , 而有不同的细节规定:《宋史·舆服》记载 , “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 , 小花如大花之数 , 并两博鬓 。 冠饰以九龙四凤……妃首饰花九株 , 小花同 , 并两博鬓 , 冠饰以九翚、四凤……(皇太子妃)其龙凤花钗冠 , 大小花二十四株 , 应乘舆冠梁之数” 。 明代贵族女性礼冠沿袭了宋代冠制 , 《明史·舆服》中有明确规定:“(皇后冠服)其冠圆匡 , 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 , 大花十二树 , 小花数如之……(皇后常服)双凤翊龙冠……龙凤珠翠冠……(皇妃)冠饰九翚、四凤花钗九树 , 小花数如之……(九嫔)冠用九翟 , 次皇妃之凤” 。 花株数量 , 图纹为龙为凤 , 为翚为翟 , 都由后妃的品级而定 。
凤冠原是后妃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的礼冠 , 至明清时 , 一般女子盛饰所用彩冠也叫凤冠 , 多用于婚礼时 。 在古代社会 , 女性缺少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 , 节日聚会可能是她们人生中难得的亮相场合 , 也是展现华美服饰的宝贵机会 。 但即便在这般场合 , 始终不能错乱的仍然是等级秩序 , 如《红楼梦》写元春元宵节省亲 , 府中女眷“自贾母等有爵者 , 皆按品服大妆” , 也就是说 , 无论个人喜好如何、财力如何 , 古代女性妆饰都受制于自己的身份地位 。
在古代社会 , 女性依附于男性 , 被隔离在公共生活之外 , 缺乏独立的人身权、财产权 , 而那些远胜于男性服饰的节日盛装 , 其实是社会对她们的某种补偿 。 德国学者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提道 , 当女性在公共领域寻求突破的冲动被阻碍时 , 就只能转向追逐时尚 , 以满足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 。 而美国学者凡勃伦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 缺乏财产独立权的女性是在“代理”男性进行消费 , 她们消费得越奢华 , 就越能体现男性的荣耀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无论是身为诰命夫人的贾府贵妇 , 还是西门庆家的妻妾 , 她们的服饰彰显的都是贾家、西门家的财富权势 。 无论那些服饰如何昂贵华丽 , 却始终折射出她们不自由、不自主的生存状态 。
事实上 , 传统社会女性的人生 , 犹如菟丝附蓬麻 , 一旦夫家败落 , 富贵便如逝水 。 《金瓶梅》第八十九回 , 清明节吴月娘穿白色孝服给西门庆上坟 , 遇到以前被她赶出家门的丫鬟春梅 , 已经成为守备夫人的春梅装扮一新 , “头上戴着冠儿 , 珠翠堆满 , 凤钗半卸 , 上穿大红妆花袄 , 下着翠兰缕金宽斓裙子” 。 两相比照 , 浮沉各异势 , 说不尽的命运吊诡 , 人生无常 。
与传统社会的女性相比 , 今天的女性无疑是幸运的 。 随着女性权利的提升 , 经济地位的提高 , 她们在时尚领域也逐渐摆脱消费代理的依附状态 , 有了更自由的选择 , 女性服饰时尚的个人化、自主性也成为当下时代文明、包容气象的重要表征 。 在妇女节来临之际 , 回顾我们一路走来的历史 , 不忘过去 , 不畏将来 , 撷取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华 , 寄望于女性群体未来的多彩美丽 , 这或许才应该是我们对传统节日服饰的最好怀念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推荐阅读
- 古代最有钱的县城大街,位于山西,现为世界遗产!
- 盘点古代十大剧毒,看看你身边有吗?
- 古代墓地风水十不向秘诀,墓地最佳风水坐向及朝向的吉凶
- 《偃师造人》中国古代第一部科幻小说
- 古代名画里的“女主角”,每个都是一段历史
- 古代没有狂犬病疫苗,被狗咬了怎么办?历史说人类终将战胜疫病
- 高三历史总复习:古代经济经济结构和特点考点讲解(人民版)
- 没有火柴和打火机的古代,人们是如何“生火”的
- 在古代谁可以在紫禁城里骑马?不是前空姐之流能进去撒欢的(图)
- 在古代,男女佩戴玉石还有这样的讲究!